


一般城市内一些正式的比较大型的葬礼应注意如下4点:(如需了解农村或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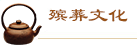
发布者:admin发布时间:2014-02-25 17:33:42浏览次数:362
也许是对文学的钟情,也许是记者职业使然,我对一些文化名人由仰慕、求教到相知、访谈,有的还成为“忘年交”。这些年高德劭的前辈不假天日,相继溘然驾西,彼此幽明永隔,但是,他们的音容笑貌常浮现眼前,其谆谆教诲仍萦绕耳际,那份情感,那份思绪,那份缅怀,总在我的胸中挥之不去,尤其是到了清明扫祭时,我默立于墓前,更是潸然泪下,追思不已……
“童心论”刻上了墓碑
谒陈伯吹墓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,童蒙开启时大多读过儿童文学。那些充满吊诡情节、富有浪漫色彩的童话引领着孩子进人文学世界。我的儿童时代,在读安徒生童话、格林童话的同时,也读了陈伯吹的《阿丽思小姐》等作品。倘论我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,这位前辈堪称我的第一位“启蒙老师”。
转眼,我成人了,并忝列了作家之末。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参与编写《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辞典》,主编陈孝全教授将陈伯吹作品《阿丽思小姐》及其姊妹篇《波罗齐少爷》、《畸形的爱》(长篇小说)、《誓言》(诗集)条目交我撰写。为更多地了解其创作背景和动因,我贸然造寓求教。之后交往频繁,访谈甚多。
访谈最多的是1960年那场对陈伯吹“童心论”的批判。
陈伯吹不仅有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,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、探索儿童文学的理论,“童心论”即是其一。1956年,曾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的陈伯吹发表了《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。就在这篇文章中,他说了那段后来受到批判、但影响一直颇广的话:“一个有成就的作家,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,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,以儿童的耳朵去听,以儿童的眼睛去看,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,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、喜欢看的作品来。”
这段至理名言竟然刻上了陈伯吹的墓碑,足见他笃信“童心论”的矢志不渝。
陈伯吹是上海市宝山人。他叶落归根,安葬于宝山区的宝罗暝园。陈伯吹之墓由两部分组成:一是厚厚的一堵墓墙,高1.5米,宽2.5米,深褐色的花岗岩上鎏刻着“陈伯吹先生之墓”七个硕字;二是墓墙前以打开书卷的形式,平卧地摆放着一块别具一格的墓碑,上书:
“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,以儿童的耳朵去听,以儿童的眼睛去看,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,…….
陈伯吹”
白底红字,分外亮丽。墓地四周由低沿的石砖围砌,墓墙前和墓碑周围簇拥着鲜花和绿草。我默然肃立,凝视着墓碑上的那段话,似乎感到陈伯吹在这方恬静的天地里,还是在诵咏着“童心论”……
当年陈伯吹的“童心论”是被当做“修正主义黑论”受到火力密集的批判。我很同情这位前辈,更佩服他对“童心论”的不懈追求,他在事过30多年后还坚持说:“如果能够儿童本位一些,可能发掘来的作品会更多一些;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,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,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,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危险”。孱弱的身躯裹着的是一副铮铮铁骨!我对他油然而生敬意。
在我记忆中存有陈伯吹和我党关系的一段轶闻,鲜为人知
1927年8月,在自己家乡执教的陈伯吹经地下党员黄忆农介绍入党。翌年2月,黄被捕,陈伯吹受到警方监视并被拘,后由当地教育局局长和校长的担保才获释。为避再次罹祸,是年年底,陈伯吹离开家乡上大夏大学求读,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。在半个多世纪的坎坷人生旅途中,他始终不渝地热爱党,追求真理,盼望着有一天重新回到党的怀抱。1983年,这位年望八旬的老作家终于实现了夙愿这是他第二次在党旗下宣誓……
陈伯吹是将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作为党的事业来尽心尽责,全身心投入。1981年,他捐出毕生积蓄,设立“儿童文学园丁奖”,1988年改为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。凝视着刻有“童心论”的墓碑,我虔诚地躬身……
常青树深深合抱生根
谒辛笛、徐文绮夫妇墓
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研读现代文学史时知晓我国“九叶诗派”中有一位“辛笛”。后进了《上海法制报》社,经同仁陆萍引见拜访了这位名闻遐迩的著名诗人。
绽开笑意的面庞,略带嘶哑的声音,沉稳缓慢的步履,娓娓而道的谈吐,至今仍深深刻在我的脑壁中,难以释怀。每次造访,或忆文史掌故,或谈创作背景,或诵诗歌新作,或论文坛现象,其思路清晰,立论犀利,融古烁今,令我每每有启迪,有教益。我将这些交谈整理成文,相继以《在中西诗艺交汇点上探索》、《西谛和辛笛的书缘》、《一颗早殒的晨星记1947年文艺杂志“民歌”》为题,刊发于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学报》、《文艺报》等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上世纪末,辛笛主编《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》,约我参与编写。得知我曾经写过论文《“七月诗派”抒情的意象艺术》,他便将“七月诗派”的条目写作任务交与我。期间交往频繁,得益匪浅。
2004年1月8日,辛笛仙逝,文坛痛失一位“重量级”人物,而我呢,则是痛失了一位“忘年交”的恩师。
辛笛的墓安放在本市青浦区福寿园内,与其相濡以沫整整一个甲子的爱妻徐文绮合葬。墓地的设计颇为奇特、优雅:墓碑的形状是一本打开的大书,右边刻有五行竖写的文字,列出两位逝者的主要文学成就“手掌集、夜读书记、辛笛诗稿、印象*花束、嫏嬛偶拾、听水吟集作者辛笛”;“狄更斯长篇小说、尼古拉斯*尼可尔贝徐文绮等译”。左边刻有“父诗人辛笛”和“母教师徐文绮”的生卒年月及立碑者。碑的前方铺有一块大理石横条,镌有辛笛《航》中的一行诗句:“将生命的茫茫脱卸与茫茫的烟水”。墓碑的右边立着一方书影,是《手掌集》的封面。作为“九叶诗派”的代表作,创作于1948年的《手掌集》是辛笛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最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上乘之作,将它的书影立于墓前,与逝者相伴,足见这些“以全生命来叫出人民的控诉”的诗篇的历史地位。
镶嵌于墓碑左上方的是一帧辛笛、徐文绮的合影,显得那般的和善、慈祥。记得当年我拜访辛笛,徐文绮总是陪伴于侧,形影不离,还不时发表一些意见,两人“桴鼓相应”、“灵犀相通”。当时,我萌生出一个念头:何不写一写这对恩爱夫妇?于是,我有意识闲聊、采访、收集素材,写了《常青树深深合抱生根记著名诗人辛笛和徐文绮伉俪情》一文,刊于1989年9月号的《现代家庭》杂志。
今年清明,我再次谒墓,向我素以敬歆的两位前辈献上一束鲜花,并久久忘返,与之进行了一番阴阳两界的“对话”……
他在上海奋斗了半个世纪
谒胡万春墓
浙江有个最大的湖,位列宁波之东,承纳钱埭之水,故称“东钱湖”。元人袁士元诗云:“尽说西湖足胜游,东湖谁信更清幽”。也许是山水清幽的自然环境,也许是叶落归根的故土情怀,著名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墓就坐落在东钱湖畔的“象坎山庄”。
“象坎山庄”是一个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式公墓,据当地人说,鄞县(今为宁波市鄞州区)象坎村人大多安息于此,即使闯荡在外的鄞县故人也往往会重返故土,长年与家乡的山水为伴。胡万春即是一例。
我与胡万春是同乡。在日前祭祀先人时,我不期而然地发现了胡万春的墓,驻足凝视,心绪连翩。
胡万春的墓列于“象坎山庄”中部干道的左侧,相比左邻右舍,它称得上是“豪华”的了:松柏环绕,石栏界地,硕大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“父胡万春之墓”六个大字,字的上端镶有一幅墓主身着西装、戴着眼镜、面慈目秀的遗照,墓穴前设有一石桌、四石凳,尤其是那块兀立于墓地左端的介绍墓主生平的碑文,洋洋洒洒七八百字,还配有一张胡万春灯下窗前写作的瓷照,更是与众不同。胡万春仙逝于1998年,2001年移葬于此。
我素来仰慕这位工人作家,甚至可以说,是读着他的作品成长的。我识文断字后,读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便是《骨肉》,至今还能忆及旧社会那个工人家庭家破人亡、骨肉分离的悲惨情景。胡万春属于上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工人作家队伍中的翘楚,多以描写产业工人的劳动与生活而活跃文坛。文化圈子里的人都说胡万春对生活有激情,健谈,也善于讲故事,我想,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作家,绝非偶然。虽说他的早期作品所描写的城市底层生活,在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观念之下,人和事不免存有简单化、概念化之虞,但它们依然以人间常情打动了我,打动了众多的读者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是胡万春创作的鼎盛期,他的短篇小说《一点红在高空中》被茅盾赞誉:“这是抒情诗,也是风景画”;1964年,在全国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上,胡万春独占鳌头,竟有两部多幕剧获奖(根据他的中篇小说《家庭问题》改编的《一家人》和中篇小说《内部问题》改编的《激流勇进》)。我曾读过胡万春写于1983年的自传体长篇《苦海小舟》,也完全赞同将其编入《七月在野*八月在宇》丛书的主编王安忆所言:“我们可以在《苦海小舟》中找到《过年》和《骨肉》的故事轮廓,就像是这两篇小说的素材,显露出感性的面目,过去的生活这一回以私人经验的性质进入胡万春的创作,不期然地,展现出更宽广的社会场景。”
我有幸与胡万春谋面一回。那是1989年底,他在凯旋路武夷路交口处开设了一家书店。我参与编写的《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辞典》一书出版,经上海作家协会引荐,我贸然登门希望能帮助推销一些。他热情接待了我,还一口允诺包销100本。当时,我真的很感动,也很感谢他!一面之缘,难以忘怀。
胡万春的墓前,鲜花簇拥,供品繁多,炷香缕缕清烟萦绕,想见他的眷属或“粉丝”刚祭扫过。我深情地注视着这位著名工人作家的遗像,默默地说:您在上海奋斗了半个世纪,上海人民永远铭记着您的英名!
扫一扫关注我
